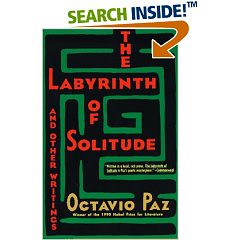SMS記事:晚上的吐露港
晚上的吐露港,除了陣陣晚風,吹來撲鼻的海水味,還有二胡聲,那是老人家三五知己坐在海旁唱曲的聲音。
我有四年左右沒有單獨來過吐露港了,上一次是高中的事。那時逢星期五晚也會跟單車黨同學去打球,夜了再聯群結隊來到這個老地方。現在單車黨都大了,我們很多年沒有見面,我想他們都因著不同的原因各散東西,有的甚至不再住在大埔了。兩三年前,大埔的中小學鬧起恐慌來,因為從統計署的數據顯示,大埔區的出生率在十八區之中最低,令學校怕收生不足需要關門大吉,難怪今晚在吐露港海濱公園見到的,也是老人家和十六七歲的居多。老的不用在家弄孫, 可以走到海邊執起二胡,相信是大埔的孩子不肯轉世投胎,為老人家帶來偷得浮生的歷史時機。他們的音樂在告訴我, 不弄孫也可以為樂,而他們喜歡到吐露港,是有他們的原因。
不少住在大埔的老街坊,也知道吐露港的兩邊以前是個石灘。媽跟我說過,廿年前會帶我們來拾貝殼,後來吐露港公路要擴建,於是要填了石灘,才能保留公路旁的單車徑,所以石灘消失了。而吐露港的另一邊石灘,就是回歸前後填的,現在已加建成海濱公園和長廊,原因是跟回歸後的地區文化政治工程有關。
這一邊的石灘,聽說是英國接管大埔時登陸的地方。怎料海軍到來的時候,遭沿海的大埔原居民用土製武器反擊,他們一直守著海岸,英軍因被迫撤退過,最後要花上兩星期,才能增援登陸。 聽一位大埔區的原居民區議員說,這段不光彩的殖民歷史,在回歸前一直沒有官方記載,而殖民政府甚至將石灘填了,大興土木建成了公園。回歸後,工程早已落成,但公園中心又再加建了一個「回歸塔」。在塔開幕的日子,有關當局還於入口放置了一塊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提字的牌。另外,現在由區議會主辦的大埔區古物古蹟導賞大使訓練班,也會跟導賞員說英軍登陸的歷史,還會將吐露港拉到明朝,說當時吐露港發現真珠,駐守港的軍旅遂捉拿漁民,用繩綁著他們的腳,迫他們潛下海去找真珠,直至找到才能上岸。訓練班的導師說,這段歷史表現大埔區人民貢獻鄉土的精神。
如果說歷史的呈現,是不同知識與權力角力的空間,那麼吐露港的歷史,就是一個教案。這些故事,在玩二胡和唱曲的老人家之中,都耳熟能詳了。我一直走到吐露港的盡頭,眼前是大埔的彼岸馬鞍山,岸邊的海景被高高的豪宅佔據了。大埔的彼岸是另一個世界,我興幸腳下的土地不屬於發展商,如果我在百年歸老的時候,還有機會跟老伴在此弄二胡,我願意在大埔善終。